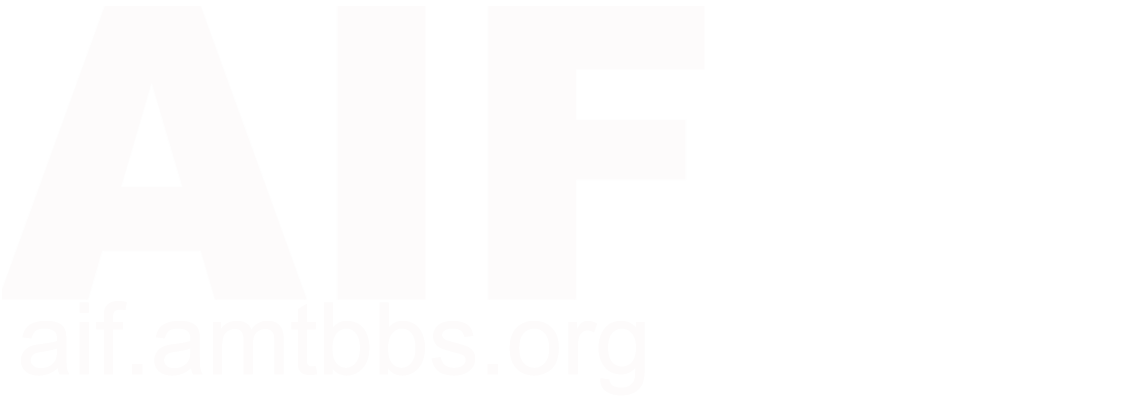作者|夏洛克
来源 |逍遥法外夏洛克导语:投资者和企业自身都需要对 Reverse CFIUS 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标准,能够明白自身投资或融资时会否涉及违反法规规定,如何在投资文件中做好约定,来保护好自己。上个月底,AI公司“蝴蝶效应”(Butterfly Effect,即Monica 和 Manus的开发公司)完成了新一轮融资,由美国老牌投资机构「Benchmark」投资。笔者此前曾介绍过,当时,我们提出过有关Reverse CFIUS的问题:
美国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和投资,是否也在释放一种积极信号:在 Reverse CFIUS的铁幕于今年1月2日正式落下后,美国投资人仍然对中国AI项目抱有相当的关注,并没有完全退潮离场?
不过,至少现阶段完全专注在海外市场的「Manus」接受“美国投资机构”的投资,到底从哪些方面涉及Reverse CFIUS,其实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好问题这或许涉及到「蝴蝶效应」的境内外股权架构、Manus的主要经营地区和收入来源、Founder身份等多方面的因素,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展开讨论。
结合近期笔者对Reverse CFIUS的梳理和介绍,今天我们用Manus来做例子,看看它到底从哪些方面可能涉及Reverse CFIUS。
根据此前两篇文章的梳理,在判断一家企业接受美国基金的投资是否会涉及 Reverse CFIUS 的管辖时,我们需要围绕Reverse CFIUS的「基础四要素」来判断,即“美国主体”、“受限主体”、“受限业务”、“受限交易”。

在 Manus 的案例中,则主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:
创始人的国籍,是否会被认定为“美国主体”?
企业本身的股权架构,是否会被认为是“受限主体”?
企业产品的主要营收地区,是否会导致其被认定为“受限主体”?
企业主营业务是否涉及“受限业务”?
创始人的国籍从 Reverse CFIUS 的角度来看,创始人的国籍和绿卡持有状态将实质性影响结果。如果“蝴蝶效应”的创始人被认定为“美国主体”,则他创业并持有中国 AI 公司(且满足一定标准)本身可能也会受到限制;如果他被认定为“中国主体”,则美国基金向他的公司投资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落入 Reverse CFIUS 的管辖。那如何了解创始人的国籍和绿卡状态?绿卡状态肯定是无法通过一般公开渠道了解到了,不过国籍状态有一个野路子可以侧面印证一下。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或者企查查、天眼查之类的公开平台上,可以查询到“蝴蝶效应”的境内主体,“北京红色蝴蝶科技有限公司”的法定代表人为“肖弘”(以中文显示);而一般对于加入了外籍的法代或者高管而言,前述平台一般会显示其外籍护照上的英文拼写(例如 XIAO HONG)。当然,这种办法的准确率肯定不是100%,受限于数据更新的滞后性,也存在一些国籍发生变更但高管名称尚未变更的情况。我们这里先假定创始人的国籍为中国籍,未持有美国绿卡。在这种情况下,创始人本身是不会受到 Reverse CFIUS 的管辖。但是,如果作为中国籍的创始人控制的“蝴蝶效应”公司从事了人工智能领域的“受限业务”,则美国投资人(比如本轮投资的Benchmark)去投资它的时候,就有可能会受到Reverse CFIUS的管辖。因此,接下来需要分析“蝴蝶效应”会否被认定为“受限主体”,这可以主要从下述2个问题着手:
“蝴蝶效应”的股权架构是怎样的,会被认定为“受限主体”吗?
“蝴蝶效应”的主营业务,会使得企业被认定为“受限主体”?
企业的股权架构与主营业务从 Reverse CFIUS 的角度,企业在以下2种情况下会被认定是“受限主体”:
「直接从事」受限业务的「中国主体」在假定创始人是中国籍且未持有美国绿卡的情况下,创始人直接持股并控制的“蝴蝶效应”开曼公司,一般会被认为是中国人控制的中国主体。如果其还从事“受限业务”,则会被认定为“受限主体”。
「间接关联」且「深度依赖」受限业务中国主体的「任何主体」这就需要拆解“蝴蝶效应”的架构是否能够满足「间接关联」和「深度依赖」这2项要求。我们一个个来看。
不过,由于“蝴蝶效应”并未上市或公开披露自己的股权架构设计,目前的股权架构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推测和假定的,如下所示:
从这个股权架构来看,“间接关联”这一条要素是满足的:境外的开曼主体最终持有境内公司的股权或实际控制境内公司。而要判断是否满足“深度依赖”的要求,就需要分析“蝴蝶效应”的各个产品的主营地区是否来源于境内公司,且境内公司的财务贡献超过 50%。目前,从公开渠道来看,“蝴蝶效应”的主要产品和运营公司如下:
Monica 网页插件:新加坡公司
Monica APP:香港公司
Monica APP 中国版:中国境内VIE公司
Manus:新加坡公司
可以看出,企业的核心业务基本都由新加坡公司和香港公司持有。虽然我们无法实际看到财务数据,但合理推测,“蝴蝶效应”集团公司的主要营收应该由海外公司贡献,中国公司的财务贡献不一定能达到 50%以上。因此,在“深度依赖”这一条要素可能是无法满足的。换句话说,“蝴蝶效应”因为这一条而被认为是“受限主体”的可能性相对较低;但其更可能因为上述第一种情况的标准而被认定为“受限主体”(前提是这家开曼公司的中国股东的股权或表决权超过 50%)。这就要进一步分析,“蝴蝶效应”从事的业务是“受限业务”吗?
主营业务有不少朋友可能会认为,既然“蝴蝶效应”从事的是AI业务,而Reverse CFIUS本身限制的就是人工智能领域,那岂不是“蝴蝶效应”的主营业务肯定就是“受限业务”了?其实未必。目前Reverse CFIUS规定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比较复杂,我们可以简化记住 1个数字即可:10^23。
只要开发超过10^23 运算量标准的算力的AI系统,都可能会落入到Reverse CFIUS的限制范围中。那么,“蝴蝶效应”的 AI 算力是否达到了上述标准?很遗憾,除非拿到“蝴蝶效应”对于其 AI 产品的核心数据,否则没有办法能准确判定是否达标。但是,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产品本身找到一些判断的侧面依据。Reverse CFIUS对人工智能的限制在于“开发”AI 系统,而何为“开发”则有比较大的解释空间。Reverse CFIUS将“开发”界定为“参与任何在批量生产之前的阶段”,例如“设计”或“实质性修改”。对于“蝴蝶效应”来说,市场对其的负面评价恰恰在于其并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,而仅仅是“缝合怪”或“套壳王”,只是将其他已有的大模型或 AI 工具进行了整合和优化。这种整合和优化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是“开发”呢?进一步来看,如果被认定为“开发”,则这种整合和优化所需的运算量还能超过10^23吗?这个问题是有争议性的。不过,从产品的实际效果上看,“蝴蝶效应”实际涉及“受限业务”的可能性,也许是相对较低的。
总结基于上面的分析,我们可以发现,“蝴蝶效应”确实可能是“受限主体”,但其主营业务有可能不是“受限业务”,进而导致“蝴蝶效应”接受美国投资者的投资,有概率其实并不触发Reverse CFIUS。这和大众的common sense好像有所相悖。传统印象里,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公司,专注于 AI 赛道,还拿了美国人的钱,这怎么可能不被 Reverse CFIUS 拦住?这里的核心原因在于企业从事的业务不一定能够达到10^23的算力标准,从而不属于“受限业务”。“蝴蝶效应”的这类情况,在目前的 AI 投资中,其实并不少见。这就需要投资者和企业自身都需要对 Reverse CFIUS 有一定的认知和判断标准,能够明白自身投资或融资时会否涉及违反法规规定,如何在投资文件中做好约定,来保护好自己。最后,也有一些衍生问题,供大家思考:
如果“蝴蝶效应”的业务达到了“受限业务”的认定标准(10^23的算力标准),那美国投资人 Benchmark 投资“蝴蝶效应”,还会受到 Reverse CFIUS 的管辖,进而存在合规风险吗?
如果“蝴蝶效应”创始人的国籍是美籍,或者其持有美国绿卡,结论会有什么区别吗?
如果“蝴蝶效应”主做国内市场(而非现在的海外市场),其国内子公司对集团公司的财政贡献占比超过了50%,会对结论有什么影响吗?
文章来自:人工智能实验室
![]()